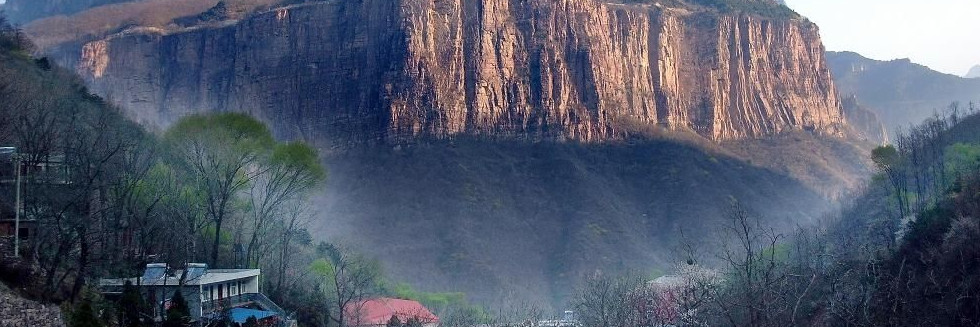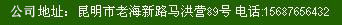|
从中国政区边界演变的历史来看,①由于封土建藩、异地垦荒、屯田认粮、改土归流等原因,政区参错不齐和界线混淆不清的问题长期存在。明清时期,以飞地、嵌地、插花地为主要表征的边界乱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妨碍管辖,流弊实深。②在封建社会时期,政府的管理事项较为简单,对此总体上以包容为主,未曾彻底予以整理。③自清末“新政”开始,政府对辖区的治理日趋细密化。“新政”期间在推行城乡地方自治时,已触及边界整理,但旋随清朝灭亡而中断。④民国时期,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政区边界矛盾全面激化,国家开始彻底整理界务。南京国民政府的依法勘界虽取得很大成绩,但远未实现勘齐全国省县边界的目标。 民国时期的省县边界纠纷和勘界迄今仍是民国史研究的薄弱领域,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⑤关于民国时期西部民族地区的省界纠纷与勘界,目前还鲜见有人论及。本文重点对甘青省界纷争进行考察,以期凸显民国勘界在西部民族地区所遭遇的困境。通过对甘青省界问题的透视,可以观察到国家无力西顾情况之下中心与边缘的独特关系,有助于从一个新视角解读民国时期的国家结构与政治特性。 一、省界纠纷凸显与依法勘界的提出 民国政府全盘承接了明清政区边界混乱的历史包袱。北京政府时期,除旧有边界纠纷继续上演外,⑥随着政区调整和经济开发程度提高,新的边界纠纷被引发。北京政府为应对严重的边疆危机,加大对蒙藏地区的管辖力度,-年下令成立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4个特别区。⑦这是年东北建省后全国行政区划的一次大变动。特别区建立后,内蒙古地区过去被蒙汉二元体制掩盖的边界矛盾表面化,陕绥划界案由此发生。绥远特别区成立之初,长城以北伊克昭盟南部晋陕甘三省共9个县的移垦区仍归该三省管辖。年1月绥远特别区都统蔡成勋以勘齐疆界为由,呈请国务院将该三省移垦区划归绥远。院令一出,陕北六县组织“争存会”,发起请愿抗议活动。几经波折,年10月陕绥划界“暂缓施行”。⑧民国时期,采用资本主义企业组织形式的农牧垦殖公司日趋兴盛。⑨垦殖公司若开发的是无主荒地或省县内官地,不会发生界争。但若进军省县界区的共有湖滩荒地,界争则不可避免。苏皖丹阳湖这桩省界大案就肇端于年安徽两家开垦公司对该湖区滩地的领垦。⑩省界纠纷尽管有追加之势,但北京政府时期因政局混乱,“无统一健全之中央政府以图改革,无完备之法律以资依据”,(11)政府未去主动整理界务,界区人民仍得以在各认其粮、各纳其税的状态中暂且相安。 年国民党完成北伐,宣布进入“训政”时期后,为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将孙中山《建国大纲》规定的县自治列为“训政时期最重要之工作”付诸实施。推行县自治必然要划分自治区,而划分自治区又须以划清辖区边界为前提。“现值厉行自治之时,县为自治单位,如疆界不齐,于划定自治区时,必多窒碍。”(12)内政部年7月制定的《训政时期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内部主管事务进行程序表》,将“厘定全国各县区划”明确列为明定行政系统的程序之一。(13)随着国民党强化基层管辖和主动清算边界乱象,边界争夺正面化,边界纠纷大面积爆发。(14) 因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改土归流和省县一体化政策,(15)边疆民族地区政区变更幅度远超过北京政府时期。年9-10月间国民政府下令热河等4个特别区连同青海、宁夏一并改省。(16)-年7年间,全国除增加6新省外,还增设6院辖市、11省辖市、76县、19设治局和4特别行政区。(17)政区建制的快速扩张,必然使边界频繁变更,不但激化旧有边界矛盾,甚至造成新的边界纠纷。宁夏、绥远两省陶乐湖滩争界案,河北、察哈尔两省旧口北道十县划界案以及本文重点讨论的甘青省界诸案,均与政区变更密切相关。(18) 省界矛盾的凸显,将掌理职方的内政部推至前台。两省争执不下时,内政部不得不出面调处。但因无章可循,面对两省各自援引历史证据,内政部难以判断,坦言:“近年行政制度,改革频繁,各省市县疆界,或因区域变更,不无参错。或因旧界淆混,迭起纠纷。先后经本部会同各省市政府核议勘划,久悬未决之案,不下十数起。只以无一定之标准可资根据,审议时每感困难”。(19)这说明,随着纠纷的大面积发生,过去依靠地方调处或由中央政府个别处理纠纷的办法已无济于事。要从根本上消除边界纠纷,就必须由中央政府制定全盘计划,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有勘界标准。年6月12日,经国民政府令准,内政部公布了《省市县勘界条例》,明确规定行政区域编制以“土地之天然形势”、“行政管理之便利”等客观地理条件和实际管辖需要为定界原则,具体界线划分以“山脉之分水线”、“道路河川之中心线”等为标准。(20)《省市县勘界条例》的颁行,开启了规范划界和依法勘界的新道路。作为对《省市县勘界条例》的补充,内政部年3月制定《县行政区域整理办法大纲》,列出“厘正”、“互换”、“划分”、“归并”等四种具体整理办法,使勘界法规趋于完善。(21) 在中央政府直接推动下,从年起,以厘正飞嵌插花边界和整理县行政区域为主要内容的勘界工程在全国展开。据年11月内政部工作报告,“四年以来,内政部依据呈准颁行之《省市县勘界条例》及《县行政区域整理办法大纲》,督促各省市政府,整理省市县界域,并厘正飞嵌插花地段。现在浙江全省县界域,均经依照部章重行勘定。河南省各县之插花地段及畸形区域,多数已加整理。此外如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青海、甘肃、福建、广西、山东、河北、宁夏等省县界域,亦均分别酌加改划”。(22)但实际情况并不像内政部设想的那样,只要勘界标准一立,边界争执自可迎刃而解。(23)在国家看来,国内的边界划分是国土内部的此盈彼缩,一块土地划甲划乙无根本区别,“盖省县划界,纯属国家行政上之一种便宜处分,与国界之含有民族意义者截然不同。甲省土地,固可改属乙省,乙县人民,亦未始不可改隶甲县,本无直接利害关系,自不必沿袭亡省亡县之谬说,过事争执”。(24)但实际情形却与此相反。行政边界是一条关乎重大实际利益乃至人们认同意识的分界线,凝结着政府和民众两个主体及其不同层次的本位诉求。在本位立场的支配和驱使下,勘界即使到了有章可循的时代,各方仍不愿放弃争执,致使勘界标准难以发挥作用。就勘界本身而言,勘划省界与县界一样,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难题。 对地方政府来说,主要是地方本位立场难以超越的问题。土地、矿产、森林、水源等自然资源与地方收益直接相关,对土肥水美、矿藏富集的地方,谁都不愿放弃。如甘肃宁定县陡石乡虽近在和政县城东门口,但因该区为宁定产粮之区,故宁定百般不愿划出。至于和政县飞入宁定、临夏两县的启明乡,因地瘠民贫,“各县均无所争,反而退让”。(25)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自认为“守土有责”和“保民有责”,遇到民众争界时,一般都“站在自己立场,竟有以寸土予人为觍颜者”。地方政府是勘界活动的主体,其本位立场直接对勘界构成阻力。 对普通民众来说,主要是负担不均和旧有管辖观念难以克服的问题。民国时期,由于地籍迟迟未加整理,各县田赋负担不一。另外又有县等之分,“一般来说大县的负担,多较小县为轻,大县的地划给小县,划拨以后,借口负担加重,多是反对”。(26)边界调整还涉及传统史地观念的调整,因旧习难移,也使划界深受影响。 对于掌控基层权力的豪绅阶层来说,主要是不愿失去既得利益的问题。豪绅有的在飞插地占地为王,有的与地方官府结为一体,所在地若划归另一县,其既得利益势必受损,故反对划拨最力,对勘界阻挠尤大。(27) 从边界类型来看,难题主要出在插花边界和公共边界上。飞地边界线大体上是明确的,划界实际上只是调整管辖关系,相对易于操作。插花边界因无界可循,勘界时必须重新定界,难度因而加大。公共边界是大家都有权使用但管辖权属不明确的界区,其中以公湖、公山和混牧草原为典型。勘划公共边界实质上是将共有利益变为独有利益,一方的占有必然是另一方的退出,激烈的对抗与冲突遂难以避免。(28) 从边界级别来看,难题主要出在省界上。省界实由县界连接而成,省界划分难题也不外乎上列几种,但在解决的难度上,省界实际远大于县界。省掌管县的人事、财政大权,省在处理县界纠纷时具有上对下的行政权力,故较易着力。而在省界划分上,中央对省虽具有强制力,但因处理链条拉长,环节增多,强制力必然随之减弱。在省界划分上,往往需由处于平行关系的省与省之间彼此协商进行,变数自然增多。边界大案率多省界而绝少县界的原因正在于此。 勘界属于国家行政行为,必须在政治安定和国家切实掌握地方的条件下方能稳步实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政权虽较北京政府时期大为稳固,但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未消除。加上战争接连不断,国家几无宁日。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勘界所遇到的最大难题不是行政之难而是政治之难。(29)正如内政部所承认的:“本部职掌全国行政区划,历年以来,经草拟《省市县勘界条例》及《县行政区域整理办法大纲》,呈奉令准通行遵办,并严令督饬各省市县依照部章拟具方案,积极办理,凡此均为整理固有行政区域,亦即系为改革省制、缩划省区之准备。无如各省灾匪频侵,军事未定,当局者畏纷更之多事,民众亦乐仍旧贯而苟安,因之本部原定整理现行行政区域计划未能于最近时期得到相当之成绩”。(30)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各省勘界无形中断。后方各省勘界虽仍在进行,但依然深受军阀势力和各种政教矛盾的困扰。甘青省界划分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正是民国勘界的缩影。 二、政治制衡与临循段甘青省界勘划 甘青省界是年1月甘宁青正式分省后产生的,全长多公里,是民国时期(同时也是今天)全国最长的一条省界线。甘宁青分省时,只是笼统地规定“遵照中央明令,各依其固有区域分别划归宁夏、青海二省管辖”,(31)并未实施勘界,因而留下一连串的省界问题。甘青省界可分为西部祁连山段、中部临夏与循化段和南部夏河与同仁段三大段来讨论。 甘肃临夏县与青海循化县之间本有大力加山(系小积石山脉北段)天然边界可循。明初沿小积石山筑有积石关等24处关隘,统称“河州二十四关”。(32)但受明代关内土司地的影响,临循段行政边界与天然边界很不一致。明代以前,河州二十四关内的藏族部落很多,部落首领在明初归顺并受封土司、国师名号后,其辖地遂变为土司地(一个藏族部落习惯上被称为一族,故土司地又称族地)。清初二十四关内外族地统由河州厅管辖,(33)二十四关内民地(即州县辖地)由河州卫(后改河州直隶州)管辖,大力加山天然边界与行政边界由此出现错位。乾隆二十七年()河州厅移治循化营(今青海循化县城)并改名循化厅及年循化厅改循化县,均未改变跨山而治的格局。 民国改元后,原河州直隶州分成四县,二十四关内的循化族地散入临夏、和政、永靖三县境内。临夏县境内族地散布面最广,主要分布于西乡,总面积近3万亩。(34)这些循化族地与临夏民地之间毫无界线可循,其混乱程度直可与浙皖荆州、上塘地界相埒。(35)和政县境内有韩土司九族地和牙当、川撒二族地两片循化飞地,面积约有五六万亩。(36)永靖县境内有韩家山、孔家寺、郝家塬和海家寺等四处循化飞地,面积都不大。(37)从年起,甘肃省(以下多简称甘省)依照《省市县勘界条例》整理县域边界时,曾向青海省(以下多简称青省)多次交涉和政、永靖两县的飞插地,但均被婉拒。直到年7月内政部派员勘划甘肃永登和青海互助间省界时,甘省方借机将地片较小的永靖县四块飞地勘正。(38)至于临循边界,因情况复杂,甘省一直未正式向青省提出。年以后,随着全国新县制的推行及户籍、地籍调查整理的展开,临夏、和政两县族民混杂、管辖不清的局面已难以为继。年1月,青省主席马步芳主动致电甘省主席谷正伦,提请由两省派员会商整理临循、和循边界。(39)2月25日,甘青两省所派专员在临夏主持召开清理临循边界插花地谈话会,最后达成两点共识:“自漠泥沟、姬家山庄、漠土山庄、范家庙、郭朗坪、石庙岭、罗石家、东拉岭、红崖由南向北取一直线,将族民两地互相拨兑,以西归循化,以东归临夏”;将和政县两片循化飞地划归和政管辖。(40)就方案本身而论,实属互换双赢性质。 但就在双方按照临夏谈话会方案实地勘测时,情况发生变化。马步芳于4月下旬提出将原定界线向临夏一侧东移,把深藏沟门等处60余户划归循化。(41)与此同时,马步芳和循化县长还鼓动临夏人“脱临归循”。(42)这些举动使谷正伦对青省的划界动机生疑。而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听到临循划界的风声后,托其堂兄、第81军军长马鸿宾带亲笔信在兰州面见谷正伦,坚决反对改变大力加山天然固有边界。马鸿逵在信中特别提醒说,临循划界“青府固尚有其他之目的,此不过藉口而已。土地属于国家,人民自应服从,惟应依照地势风俗人情天然之趋势……果韩家集浸假划入青省,则将来不仅纠纷无穷尽之时,且或有事故发生”。(43)马鸿逵是临夏韩家集人,而韩家集是韩土司驻地,最有可能划到青海去(实际上未划入),因此对临循划界殊感不安。马鸿逵将临循划界与临夏地区的政治安危和青宁关系联系起来,足以让谷正伦三思而行。就在马鸿逵反对划界之时,青省又提出以湟水和黄河为界调整青海民和县与甘肃永登、永靖两县之间省界。(44)照此方案,永靖划给民和的将是全县四乡一镇中的三个整乡,这与“消灭”永靖县无异。谷正伦认为青省“名为调整,实即要求甘省割让”,(45)对青省最终由怀疑转为愤怒。6月1日,谷正伦以变更省界须经中央核准为由,函告青省临循划界暂缓进行。6月10日,谷正伦分别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军政部长何应钦、内政部长周钟岳和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呈递密函,详细报告年1月以来甘青边界四起界案的由来及甘省主张,请求中央做主解决。(46) 因甘青省界事关西北后方稳定,国民党中央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经过长时间研究后,行政院于年3月15日下令甘青省界“应暂维持现状”。(47)此时循化县已自行在拟划归区域设立该县第一区(区署设麻呢寺沟),开始编组保甲户口,对该令置之不理。到年8月,循化县所设第一区已编成11保总计余户,临夏信义、永寿等乡镇混入拟划界区躲避粮差者也被编入,给临夏的征粮征兵造成严重困难。(48)被迫之下,甘省第二次将青省告到行政院。11月23日,行政院复令临循间省界“仍维原状,该循化县政府所设区署应即撤销”。(49)但仍不为青省遵守。无奈之余,甘省第三次将青省上告。年5月,行政院第三次催令青省,要求“临循两县应维持积石山西分水岭原界”,循化县在麻呢寺沟所设区署应遵令撤销。(50)但该令同样是一纸空文,恢复临循边界原状最后变成一句空话。 综观年临循段甘青划界上闻中央后的形势变化,可以看出事实走向完全背离了甘省和国民党中央预想的轨道。中央政府介入后,临循划界纷争非但未能平息,反而坠入死局。从表面看,青省违抗院令是主因。而事实上,临夏地区的特殊性、青宁“二马”主政青宁二省的特殊局面及由此产生的复杂政治制衡关系才是问题的根本。临夏旧称河州,是西北最大的回族聚居区,同时也是中国伊斯兰教诸多教派门宦的发源地,素有“中国的麦加”之称,(51)民族宗教问题历来非常突出。清代因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分化政策,临夏爆发过多次回民起义。这些斗争“在统治者的欺骗与怂恿下,则转变成民族间之矛盾与冲突”。(52)年,因反对国民军苛征暴敛,发生河湟事变,再次使回汉民族关系蒙受重创。河湟事变过后,中央政府及甘肃省府吸取历史教训,对临夏地区的设官任职及社会治理均持谨慎态度。 临循划界关涉的临夏西乡,正好是近代叱咤西北政坛的“河州三马”的桑梓地。“甘马”马安良家在漠泥沟,“宁马”马福祥家在韩家集阳洼,“青马”马麒、马麟兄弟家在癿藏,相距均不过三四十里。(53)“甘马”集团在年河湟事变中被灭,河州“三马”只余青宁“二马”。青宁“二马”的政治舞台虽然不在临夏,但与临夏的关系均极密切。这两个集团的基干全属临夏同乡同族,许多头面人物都在临夏老家置有房产、地产等不动产。(54)更重要的是,临夏是西北回族和伊斯兰教的一块高地。马步芳和马鸿逵虽同属回族军阀且近为姻戚,有许多共同利益,“但互争雄长,时有暗潮”。为争夺民族旗帜和宗教旗帜,青宁“二马”无不格外重视对临夏的经营。马步芳、马鸿逵都利用在临夏修清真寺、建学校的办法拉拢群众,扩大各自的教派势力和群众基础。在教派上,“宁夏马主席鸿逵为旧教实力派之领袖,青海马主席步芳为新教实力派之领袖”。(55)马步芳捐钱修了南关大寺和癿藏大寺,马鸿逵则出资修了老华寺和韩家集磨川大寺。(56)在兴学方面,马鸿逵在韩家集一带办有1所中学和10所小学,马步青、马步芳兄弟在临夏城关和癿藏等地建有1所中学和多所小学。(57) 从青宁“二马”在临夏的实力对比来看,“青马”占绝对优势。年中原大战爆发前夕,甘宁青三省的冯玉祥部队扫数东下。为填补甘省的布防真空,代理甘省主席王桢向青省主席马麒求援,青军遂大批开进河西走廊和临夏,掌握了这两个地区的驻防权。(58)中原大战结束后,甘肃政局波澜横生,中央力量迟迟不能到位,入甘青军在乱局中存留下来。年朱绍良主甘后推行“在安定中求进步”的方针,对遗留青军持包容政策,使甘境青防的局面长期化。(59)年河西走廊换防时,为减小对“青马”的刺激,国民党中央特许临夏青军不换防。(60)因此,临夏地区的军事权一直握于“青马”手中。“青马”还直接介入临夏的行政权。-年间,甘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驻临夏)就长期由“青马”干员马为良担任。相比之下,“宁马”在临夏无一兵一卒,明显处于弱势。但甘省是在拥有临夏地区行政管辖全权的前提下承认“青马”的既得利益的,这对“青马”的军事权有制衡作用,对“宁马”在临夏的利益有保护作用,使甘宁青三方能够在临夏达成政治平衡。 临夏西乡划界事关行政管辖权的变更,使该区行政权有落入青省的可能。若这一局面出现,甘省的平抑作用必然消失,“宁马”在此间的祖宗墓庐、田园基业不仅失去保障,而且临夏这块民族宗教高地也将归“青马”独有,“宁马”对此当然不能接受。从马鸿逵年五六月间与谷正伦的密切书信往还,足以看出临循划界对其震动之大。(61)国民党中央也看到临夏谈话会的不利影响,因此坚决不许青省突破大力加山分水岭。国民党中央最担心的是划界加剧青宁矛盾而引发教派冲突,进而危及西北民族关系的稳定。“如允青马所请,宁马必大感不快,对西北整个局势,将受不良影响”;“为协调回教新旧派纠纷起见,仍宜维持原界”。(62)这样的处理顾全了西北大局。 按照《省市县勘界条例》规定的天然形势和行政管辖便利原则,临循之间以大力加山为界是最合适不过的。但这样做有三难:一是“青马”在临夏西乡有重大政治利益和各种实际利益,断难放弃。二是青军驻防临夏,对“青马”在临夏的利益起着保护作用。在青军驻防权难以动摇的情况下,以大力加山为界无从谈起。三是从划界本身来说,甘省在大力加山以西没有飞插地,整理临循边界实际上是由甘省单方面收进青省地域。青省只出不入,自然难以接受。要排除这三难,就必须打破大力加山天然分界线。但打破大力加山天然分界就打破了临夏的政治平衡,结果行不通。临循划界虽然以青省实际占有争议界区而不了了之,但这一既成事实毕竟未获中央同意,尚不为正式结果。另外,“宁马”最为北京较好的白癜风医院白癜风医院天津哪家好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文明校园濮阳市油田第一中学加强校园
- 下一篇文章: 上海马拉松沪跑团集合补给摄影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