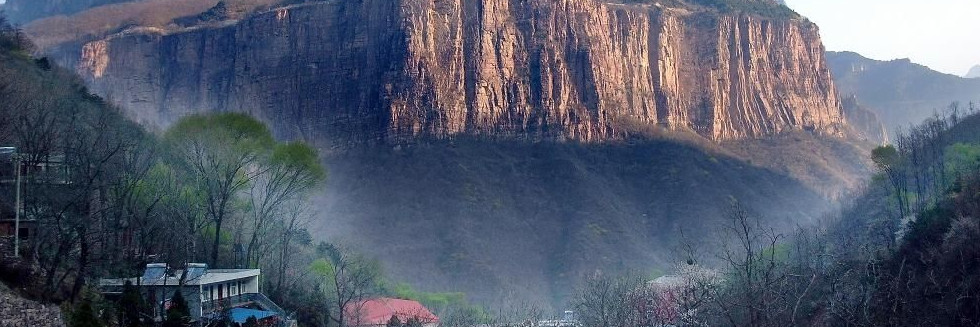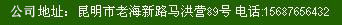|
硫磺与白癜风是什么关系 http://www.bdfyy999.com/bdf/yufangbaojian/ertongzhuanlan/m/56751.html 编者按:本月,上海踩踏事件、姚贝娜逝世报道等几个大事件纷纷指向了媒体道理伦理问题。虽然事件随着时间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对于产生问题的根源,我们还要深入地进行讨论和反思。今天我们邀请参与上海踩踏事件报道的新京报记者卢美慧,还原当时采访过程,同时也探讨应该如何报道灾难中的“逝者”。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报道 作者:新京报深度报道部卢美慧 因为对上海踩踏事故中一名遇难复旦女孩的报道,以及之后一篇复旦学子联名对媒体批评的公开信,踩踏事故前几日,舆论对于媒体的讨伐和恶语有些铺天盖地。加之之后的庞麦郎、姚贝娜以及女诗人余秀华等事件,媒体德行接连遭受诘难,大众指责媒体没人性,记者感慨大众“吃着猪肉骂卖猪肉的”,互相不对付,也算是社交媒体时代一景。 “笨拙的工作方式” 我是一月一日中午到的上海,因为自己负责的内容就是事故中死伤者的采访,医院,一刻也不敢耽误。经常会有声音说,你们记者不去报道事故原因总盯着死者家属干什么,医院的同时,另外两名同行在外滩进行着相关采访。关于该不该报道灾难中遇难者的问题,本就是个伪命题,很多同行在事件中也积极发声,在此不再赘述。 医院,大厅里就是情绪陷入崩溃的家属,哭声一片。有时候也挺庆幸自己是个纸媒记者,所以我就在大厅内守着,从中午到下午五点左右编辑催稿,什么也没有采访到。 能做的就是守着,如果有人需要搀扶或者其他帮助,会自觉地上前帮一把,然后退后。 人的情绪发泄都有个过程,一直到当天六点,一位在事故中失去未婚妻的男子才愿意开口,慢慢还原了事发时的经过。 第二天,相关报道还要继续,但因为家属们被分散安置在不同的宾馆,所以只能去殡仪馆寻找。在那里,陆陆续续又接触了几位家属,很幸运的是,在说明了采访意图之后,一位家属带我去了安置他们的宾馆,进行了更详细的采访。 以上是自身在上海踩踏事件中负责的工作内容,怎么说,这都是一种笨拙的工作方式,在前方,我看到的绝大多数同行都是采用的这种工作方式,以致后来网上口水漫天,都为那些从事发时就默默蹲守的同行感到委屈。 第三天,一封《复旦学子致部分媒体的公开信》开始流传,紧接着媒体同仁投书反驳,一时间舆论好不热闹。同样的事情在马航失联事件中也曾上演,一次次的口水战中,记者成了众矢之的,身边同行们都自嘲,没事骂骂记者,成了当下最时髦的全民运动。 如今反观整个事件,媒体自身做的并非没有瑕疵,但网上喊打喊杀乱打道德大棒未免也有些夸张。关于如何报道灾难中遇难者的问题,倒是最先想起来《新京报》的《逝者》栏目,结合当时的经历,简单说说自己的感受。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报道 记者和受访者不是“敌人” 《逝者》是新京报的一个固定版面,也是国内比较早的针对普通人的固定报道。很荣幸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中,试着联系逝者的家属或朋友、同学,说明采访意图,然后走近一个个悲伤的个体,听他们讲述逝者生前的种种。如此这般,一个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得以被记录,他们是怎样的人,在这世上曾经历怎样的欢笑或泪水,他们的希望或遗憾,都通过文字的形式定格下来。 我和我的同事们几乎都有这样的经历,起初会被拒绝,情况好的话对方会告知不想被打扰,情况不好的话可能就恶语相向了。所以那时候总会感慨,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忌讳谈死的民族。 但是既然做了这个工作,有些事硬着头皮也要去做,所以那个时候我最常跟家属说的一句话就是:纪念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种,让世人知道他或者她如何活过也是其中一种,我愿意尽力做好这件事。 沟通的结果,大多数最终会选择相信我们。还有家属在报道发出后会对我们的工作表达感激,我和我的同事们大都收到过类似的信息,老实说,那些宽容真挚的文字,至今是我工作下去的动力之一。 如今每年记者节,收到的祝福信息里一直有我报道的第一位逝者的爸爸妈妈,一次去他们家乡出差的机会,我还去了他们家里。 其实说了这么多,想说明的事实是,记者和受访者不是敌人,很多时候,因为特殊时刻的倾诉与倾听,反而会有特别的缘分。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报道 “逝者”的故事如何记录? 当然报道的过程中,尊重和体谅是一切的前提。上海踩踏事件中,确实医院对着悲痛欲绝的家属一顿狂拍,有些镜头几乎都要贴到受访者脸部,在任何灾难事件中,此类暴力都备受苛责,作为职业共同体的一员,因此被骂,觉得理所应当的同时又倍觉无奈。 但最近几次网上的争吵,总有一种声音是要把记者和受访者割裂开来,仿佛记者的存在就是吮血食骨,给悲伤的家属伤口上撒盐。 这种论调可怕就可怕在给了一些人义正言辞的机会,上海踩踏事件中,让我惊诧的并不是复旦学子们讨伐媒体的联名信,仔细说来,细究具体稿件,媒体确实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但是以不要打扰死者的名义跳出来说“请记者理解”,实在就于理无据了。 当时很多机构转发了复旦大学的那则官微,都能轻易想见,每一只鼠标背后人们义愤填膺的样子。 上海踩踏事故暴露的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交媒体信息的使用问题,在社交工具广泛被应用的今天,通过其搜集素材积累信息,几乎成了每一位记者的工作方式之一。但为什么偏偏南方周末和本报的报道在事件之初会引发那么大的反弹,究其原因还是信息来源单一。 本报关于复旦女孩的报道,是后方同事通过网络和电话采访写就,细看南周的报道也是。这其中并不能否认记者的工作以及突破能力,现代技术如此发达,后方记者有时候比前方更能发挥能量。但细究有关本次报道的争论,个人觉得,就报道而言,社交媒体信息不能也不足以成为报道主体,纯就报道而言,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它们可以做锦上的那朵花,但是做不了那块锦。反观当时我们的一些报道,确实有社交媒体信息作为主导的问题。 很显然,如果那名复旦女孩的报道中有其他信源补充,或者经过了近亲属的同意,所有的争论都不会存在。 所以最后事件的结尾是,记者没有采访到核心信源,而网上喊打喊杀的主体也大都并非女孩特别亲近的关系,在一则报道中最该出现的人自始至终没出现,只剩下不相干的人吵着各自认为正确的口水仗,不能不说非常遗憾。 个人的意见偏向于,灾难事故中的逝者报道,“快”并不是第一法则。毕竟逝者报道之所以产生并延续下来,是基于人文关怀,牺牲这部分,除了招致口水,也失去了报道的本源意义。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报道 记者就是“记录的人” 前几日上海踩踏事故的调查报告出来,收到一名遇难者家人的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即食新闻上海米其林紫外线稳坐
- 下一篇文章: 地方新闻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探索行政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