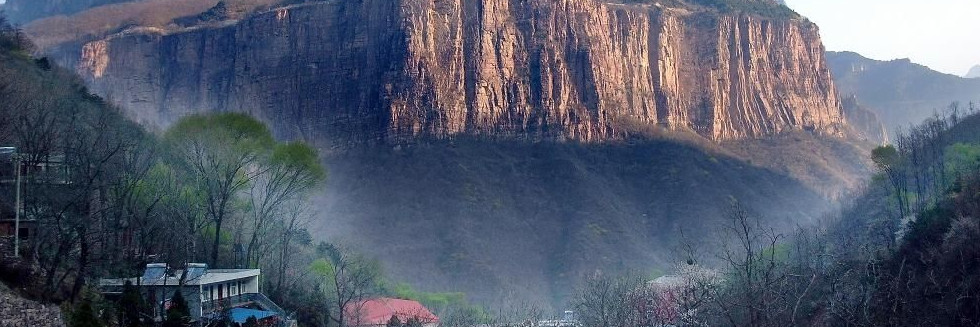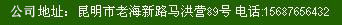|
咱郑州有个“陇海大院”,不久前成为2014央视“感动中国”候选人。 “陇海大院”是什么?一个院子?一群人?一种精神?怎么说都可以。2006年10月17日,《河南商报》A10版以《铁杆邻居轮拨儿抱他30年》为题率先报道此事。今天我们再讲讲他们的故事。 共患难 壹 邻居照顾他近40年,从少年到白头 64岁的高新海住在幸福路5号院。原来住的陇海大院搬迁,他临时被安置在这里。房间不大,床头有扶手、便盆——这是为高位截瘫的他特制的。房间相当整洁,没有一点长期卧床的人身上的味道。 每天天一亮,就有人陆续过来了。来得最早的一般是“石头”。他扶高新海起床,给他倒好水,没多久,赵新义也来了,给他倒便盆、梳头。中午,有时候有人来做饭,有时候是送饭。 这些人都是他的老邻居。 截至今年,高新海卧床39年了。1976年插队时,25岁的他突然得了急性横贯性脊髓炎,高位截瘫。没几年,他的二哥因病去世;1987年,母亲患结肠癌;1997年,大哥患肺病,卧床不起;2005年,父亲患上老年痴呆;2008年,父母相继去世。 这个家的难处,只有这些老邻居知道。从高新海生病起,他们就陪他四处求医,照顾他。大家聊天时都会感慨:“一转眼都快40年了,从少年到白头,好像只过了一夜;但又慢得很,一天一天都是数着过的。” 解心结 贰 上万个日夜陪伴,帮助他迈过生死 高新海曾是个帅小伙儿,还是足球运动员。高位截瘫后,他不止一次想过轻生。如今在他的脸上,很少再见到阴霾,尤其是这些老朋友来时,屋里常常是欢声笑语。 “三哥,屋里还放了束花,闻着香味,睡得可好吧?”爱开玩笑的刘丽娜一进门,屋里的空气都活泼了几分。 “好啥,晚上12点睡,第二天4点起。”高新海笑着说。每天他要吃大把的止痛药和速效救心丸,夜里难受得睡不着。 最辛苦的是大小便,之前他每周解一次大便,需要用四五十瓶开塞露,两个人使劲帮他揉肚子。2006年,他做了手术,才可以自己排便。 他曾经想过,如果自己没得病会怎样呢?他羡慕正常人,更感激身边这些人。他觉得,生死就是一个坎儿,迈过去了,就永远不会害怕。 天气好的时候,他喜欢出门遛遛。他有辆特制的三轮车,他经常骑着三轮车帮邻居们送人、拉东西,三轮车仿佛是自己的腿。 诉衷情 叁 “他就像我们的亲人,不可能丢下” 今年65岁的樊石头是高新海的发小,也就是“石头”。 许多时候,他默默地来到屋子里。两个人有时候聊天,有时候不说话,他知道高新海什么时候想喝水了、该吃药了,都不需要说。 3个月前,樊石头家搬到了西大街,离高新海远了,他特意买了辆车,每天送完老伴儿上班,就拐到高新海家,像上下班一样准时。 还有人称“瞎毛”的王志平。他因为眼睛有障碍,提前退休,多年来,他带着高新海洗澡、骑车。前几年,他养了一只蝴蝶犬,每次一出门,蝴蝶犬不用招呼,就直奔高新海家。蝴蝶犬死后,他又养了一只金毛犬,后来丢了。没有了金毛犬领路,王志平出门极不方便,就那也没忘过来看高新海。从他家过来那段路,平常人20分钟能走完,每次他都得挪40分钟。 这些年,大家习惯了在高新海家吃年夜饭、看球赛。在邻居们心里,他已经成了亲人,“不可能丢下他。” 话感想 肆 有他们的“陇海大院”,已成为一种精神 位于陇海路中段的陇海大院建于1913年,当时是陇秦豫海铁路总公司,住的几乎都是郑州铁路局职工。 社区主任井勇对这个大院印象深刻。他是2008年过来当社区主任的。不止一次,大院的邻居给他端来热气腾腾的饺子。 2014年4月,陇海大院面临搬迁。高新海最不愿意离开,那些老邻居说分开就分开了,但是大家还会想方设法来照顾他。当初搬迁时,说的是3年后安排回迁。“如果不安排回迁,可能大家都不愿走。”大伙说。 他们一直希望,陇海大院的人还能住到一块儿。 井勇说,“陇海大院”已经成了一个符号,一种精神,这些年,帮助高新海的人一批又一批,说不清有多少了。他们可能在单位里、在大街上都是默默无闻的,但是在高新海这个小屋里,他们却是那么重要。 部分照顾高新海的邻居 赵新义:照顾高新海生活,成为高新海的“专用”理发师。 周喜荣:郑州三院护士,多年来帮高家几口人看病、打针。 陈会云:曾是陇海大院保洁员,外号“驴”,力气大,十多年来帮忙修车、搬东西,体重180斤的高新海,他经常抱上抱下。如今,他给一家市场当送货员,虽然搬走了四五年,但经常抽空回来照顾高新海。 张海龙:照顾高新海生活,不分昼夜随叫随到。 孙豫生:常年帮高新海做饭。 杨继增:高新海在二哥去世后曾极度消沉,杨继增带着自己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住在他家一个星期开导他。 提醒 如果你也被他们的故事打动了,请为他们投上一票吧。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henanshengzx.com/hnxx/31.html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2014河南外贸规模创新高 手机成第一大出口商品
- 下一篇文章: 河南五级联动培训教师 构建教师教育终身